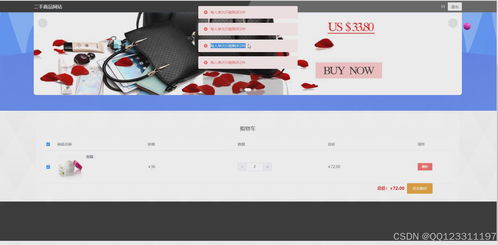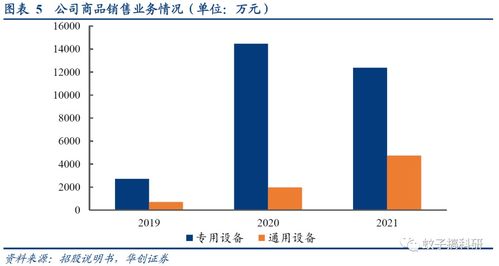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,謠言往往像病毒一樣快速蔓延。疫情期間,從“雙黃連可預防新冠病毒”到“5G傳播病毒”等不實信息屢屢刷屏,許多人甚至在轉發后才意識到自己可能傳播了謠言。這背后是復雜的社會心理、信息環境和認知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。
一、信息真空與焦慮情緒的共振
當重大危機發生時,公眾往往處于“信息饑渴”狀態。官方信息的發布需要經過嚴謹核實,而謠言卻能迅速填補認知空白。心理學研究顯示,人類對不確定性的容忍度極低,面對未知威脅時,大腦會本能地尋求解釋——即使這個解釋缺乏證據。武漢封城初期,當人們對病毒傳播途徑尚不明確時,“寵物傳播病毒”等謠言之所以廣泛傳播,正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看似具體的防范目標,緩解了人們面對無形威脅的無力感。
二、社交媒體的“回聲室效應”
算法推薦機制無形中構建了信息繭房。當某個謠言被特定群體接受后,社交媒體會持續推送類似內容,形成自我強化的信息閉環。研究發現,疫情期間,家庭微信群往往成為謠言傳播的重災區,這是因為親屬關系帶來的信任感降低了信息核實門檻。而“寧可信其有”的預防性心理,使得許多人選擇先轉發“可能有用”的信息,客觀上助長了謠言傳播。
三、認知偏差的多重作用
- 確認偏誤:人們更傾向于相信符合自己原有觀念的信息。若某人對某些機構存在不信任,那么關于“疫情數據造假”的謠言就更容易被采信。
- 情感啟發式:當信息引發強烈情緒反應時,理性判斷往往會讓位。那些描述“醫院尸體無人處理”的駭人敘述,即使后來被證實為謠言片段拼接,其造成的情感沖擊已足以讓人忽略事實核查。
- 從眾心理:看到親友紛紛轉發某個“防疫偏方”,個體很容易產生“這么多人都信,應該有點道理”的心理暗示。
四、信息素養的數字鴻溝
中老年群體成為謠言易感人群并非偶然。他們成長于傳統媒體時代,習慣于單向接收權威信息,面對社交媒體上海量且矛盾的信息時,往往缺乏必要的數字批判能力。而年輕群體雖然熟悉網絡操作,但也可能因專業領域知識不足而誤判——例如生物醫學類謠言就常利用專業術語包裝獲得可信度。
五、對抗謠言傳播的技術路徑
- 建立“謠言指數”預警系統:通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監測高頻傳播內容,結合權威機構數據庫進行實時比對。
- 發展可視化辟謠產品:將專業機構的文字辟謠轉化為短視頻、信息圖等易傳播形式,例如將病毒傳播機制做成動畫演示。
- 構建協同驗證平臺:類似“騰訊較真”的跨界合作模式,聯合醫療機構、科研單位、媒體形成事實核查網絡。
- 設計“認知疫苗”干預:借鑒疫苗原理,在謠言傳播前主動推送經過科學包裝的反駁論點,如提前普及“病毒不可能通過無線電波傳播”的電磁生物學常識。
值得深思的是,單純指責“傳謠者”往往無濟于事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曾指出,風險社會中真正的危機是“信任危機”。當我們在轉發前多問一句“這個消息的原始來源是什么”,在情緒波動時意識“這可能正是謠言利用的心理弱點”,或許就能在信息洪流中守住理性的方舟。畢竟,對抗謠言不僅是技術問題,更是現代公民在數字時代必須修煉的認知免疫力。